上海-台北两岸文学营暨小说工作坊首次采用视频连线的方式,记录下系列主题讲座和导师们的对谈;连载《虫之履》迎来第七章!各地邮局、报刊亭均有零售;邮局订阅邮发代号:4-4;网购请搜索微信小程序或淘宝店铺“萌芽小铺at萌芽”。

头条
《人需要故事,这是人的天性》
木叶主持,毛尖、小白和高翊峰、既晴的对谈《文学表述中的影像再现》探讨经验与虚构的关系、电影和文学间的互译;陈国伟主持,蔡骏、血红和陈雪、东烨的对谈《在虚拟世界中如何虚构》讨论散文与小说的边界、真实和虚构的力量;金宇澄主题讲座《老金地图——处世与表达》分享对城市生态的个人叙述。此外,文学营“盲评会”针对具体作品提出虚构意识的问题,由经典到当下,分散而又聚拢,正如詹姆斯·伍德所说:“当我在谈人物时我其实在谈真实,这是我全部探究的终点。”
小说
夏烁《他的名字》
班上的学生李梓轩邀请我们去看他演的电影,在星期五晚上,电影乏善可陈,而李梓轩又确实不适合演电影,他没有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反馈。我想起刚开学时他学习总是很用功,似乎等待着别人的认可,然而一切都白费了。外校转来的好学生李子轩也在那个学期来到我的班上,从此区分他们的名字成了问题,而他们也开始默认了一种认领名字的次序……
马广《就像被闪电击中(上)》
这是一个科幻迷对具有科幻色彩的现实事件的调查记录。大约一年前,一段标题为《太白书院有外星怪物》的视频传遍网络,之后,太白书院院长李长青遭遇严重车祸,调查于是从这场车祸开始。太白书院的“元老”老金、老金的三姑爷阿宽、李长青本人以及更多相关者依次登场,真相在其中时而庞大清晰,时而渺小难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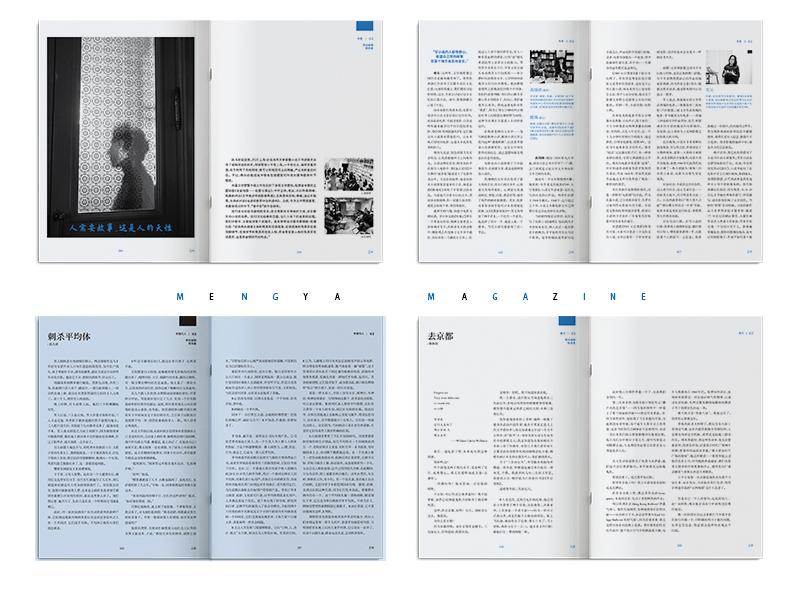
专栏
#奇怪的人#
沈大成《刺杀平均体》
“平均体”最早是一家科技公司的专利产品,在一个生化人身上概括一群人的智力、心理、形态、行为……它们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,于是自然人开始动手剔除“平均体”。昨晚,又有凶杀事件发生,与此同时,R的同事也看出了他是一个“平均体”……
#三角关系#
库里里《次等创作》
文学并不承担揭示“历史真相”的义务,相反,词语背后的形象再创作才更加重要。正如同“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”,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子并非西方文学传统中的英雄主人公,弗洛伊德与艾略特对其的解读也含有自我移情的成分,这正是布鲁姆所说的“批评的窘境”。理想的创作是心神交汇和次等创作的结合点,然而其限度却难以把握,我们不妨在次等创作中找到属于自己趣味的解读。
散文
陈秋韵《去京都》
从前和B在一起的那段并未被定义也不排他的关系里,B总调侃说“那些男孩”是我的朋友。我与他谈论文学、电影、音乐,似乎是那些符号而非真实的生活让我们相爱。后来我搬来香港生活,和B的联系逐渐只剩下一个点赞或表情。其实剥开时间和文化的外衣,我们两个都是赤裸的生命,而我爱的就是B的那点动物般天真的部分。
杨兆丰《The Moon Song》
在Fantoft居住时,我在交换生找朋友的俱乐部里独自弹吉他,碰到一个亚裔女生,她问我会不会弹她最喜欢的《The Moon Song》。后来打台球时,我又遇到了中国交换生小X,她与所谓的男朋友间虚幻、飘渺的感情令我想到《The Moon Song》的出处电影《Her》。感情似乎只是一种抽象和虚幻的陪伴,正如俱乐部里那把很快被人弹断了琴弦的破吉他。
郭宝婷《悦声响起》
我认识田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三年,我采访田,问他关于音乐创作的事,研究他的社交账号,和他吃饭,却总忍不住窥探他们的生活和那个女孩的样子,联想起自己的失恋,想我是否不值得得到幸福,而那好像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我在《极乐迪斯科》中把时间一再重复,却无法踏进田那一千多天的记忆,我知道有一天,一切都会回归平静,但那些记忆会以某种方式一直存在于那里。

惊奇
#公开课#
指间沙《麻花辫的摩登文艺系数》
麻花辫一向是清纯与美丽的代名词,有时也具有时代特征或政治立场。中国的影视剧依靠双麻花表现女主角的纯洁乖巧,乌克兰的美女总理季莫申科将金色麻花辫盘在头顶,以符合质朴、爱国、谦逊的乌克兰姑娘形象。剪辫子也同样象征着女权与自由,象征自我牺牲和已逝的青春。跨越时空转换与名称演变,麻花辫的文艺内涵在全世界都被广泛接受。
#惊奇乱讲#
惊奇组《废墟行者见闻录》(下)
人人网、博客、百度贴吧等曾经红火的社交平台已日渐沦为“网络废墟”,而今回顾,除了能在其中窥探他人生活的遗迹,保留住过往岁月的记忆,“遗民”们是否也始终渴望着能有一片精神家园能够供自己生存与栖居?
连载
察察《虫之履》(七)
我来到并不熟悉的SKP寻找“山馆”,导览图、手机地图上都没有定位,询问服务台后我坐扶梯来到顶楼,进入一扇嵌在巨幅装饰画上的门,那里有百来号人在等待,场景似曾相识,令我想起7年前第一次见到Run的情形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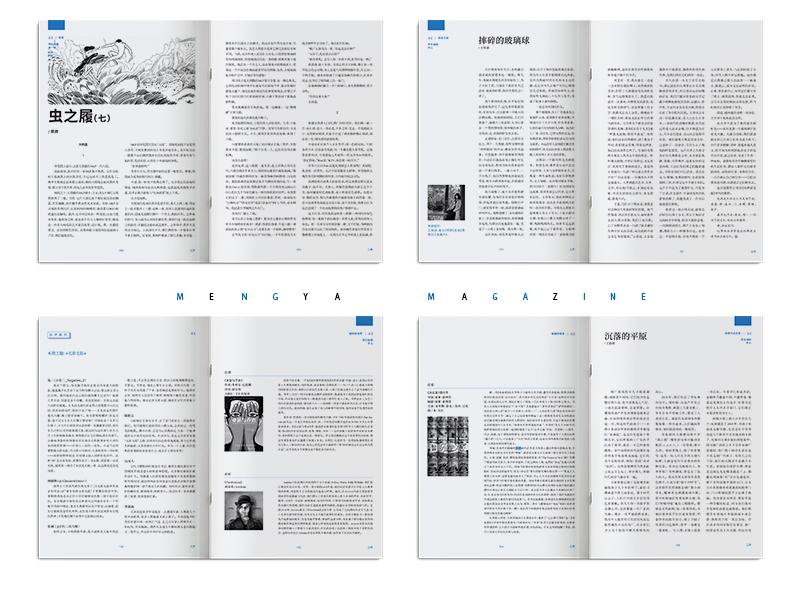
萌星月报
王笑迪《摔碎的玻璃球》
小时候的一年生日,我摔碎了刚拿到手的玻璃球,亮光和音乐在黑暗中陡然消失、变成一堆工业垃圾的那个瞬间成为我生命焦虑的象征:美好消逝,无人知晓。凌晨的醉酒,桂花的香气,我记不得也抓不住,因为那是属于人类的亘古不变的焦虑。只有写作能起到暂时舒缓的作用,对我来说,讲述成为见证的唯一办法,让记忆里的片段获得存在,有迹可循。
新概念
#参赛作品选登#
王韵寒《沉落的平原》
在房地产开发热潮到来之前,钢厂家属院的几十栋家属楼彼此相连,有电梯的几栋叫作“周正楼”,我曾和A在周正楼坐电梯,也在周正楼马路对面的红顶黄楼里远眺。几年过去,我们逐渐没了话题,钢铁产业也不再勃兴,所有人都在向未知的地方飞去,不论是否掩藏起绝望,停留在时代的浪潮里终究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。
#新概念书写#
陈虹羽《我曾看见一只飞鸟》
我在一个小城市中出生与成长,直到初一时才从语文老师分享的“新概念”获奖作文选中明白,写作和写作文原来并不是一回事。我开始向新概念作文大赛投稿,2006年第一次坐飞机来到上海参加复赛,此后,生活再次回归平常。大学时我阴差阳错读了文学系,又开始在《萌芽》上发表作品,之后留在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社实习,直到后来决定辞职全职写作,如是一切与幼时的想象全然不同。写作不再是我仰望的飞鸟,而成为了我赖以生存的技能,它给我带来的满足与幸福也往往能抵消掉那些折磨。
#大赛专栏#
“长江文艺”杯第二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初赛评委名单





